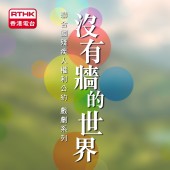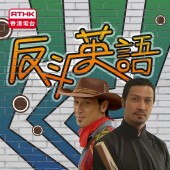遇见香港作家
4 related episodes
虽然香港常被讽为文化沙漠,但其实也出现了不少著名作家,看看作品的同时,我们也可在节目中窍探他们的另一面!
 Loading ...
Loading ...《遇见文学》 第二辑 #14 作家:金庸
2017-05-14
返回
《遇见文学》 第二辑 #14 作家:金庸
2017-05-14
金庸,原名查良镛。武侠小说泰斗,自1950年起,以笔名『金庸』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。今集介绍他的最后一部作品《鹿鼎记》,这部作品被喻为是他的巅峰之作,它不单集之前的作品之大成,而且还颠覆了武侠小说的定义与想像。